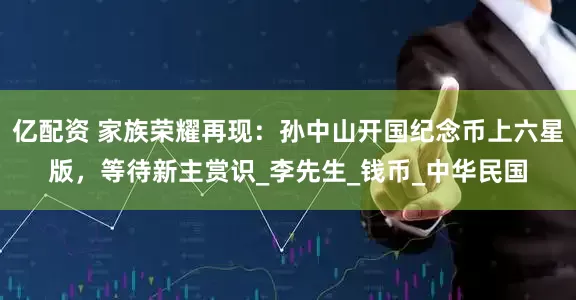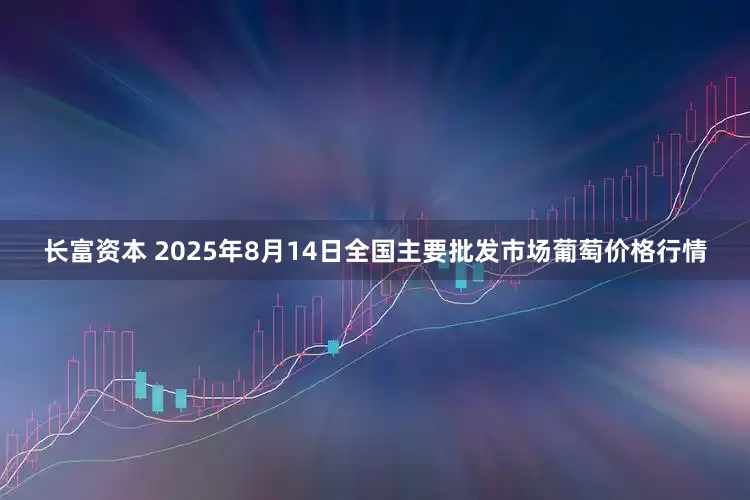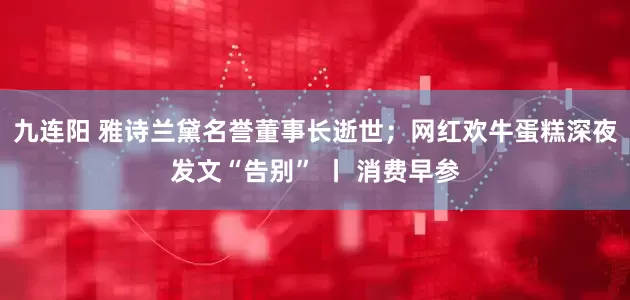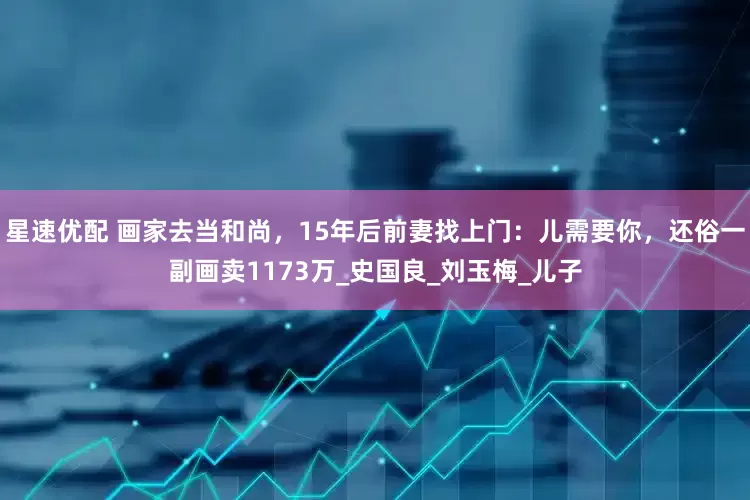
好的,我帮你将文章每段做语义相同但更丰富细节的改写星速优配,整体字数保持相近:
---
当代一幅画作竟然以高达1173万元的天价被拍出,而令人惊讶的是,这幅价值连城的画竟出自一位和尚之手!一般人印象中的和尚,多半是清心寡欲、超脱尘世的象征,他怎么会参与到如此商业化的艺术交易中呢?这是否违背了佛门“清规戒律”?事实远非如此,因为这位和尚其实早在2010年就已经还俗了。
这位有着“画僧”美誉的史国良,曾经做了整整十五年的和尚。面对妻子刘玉梅的深情恳求,看着家人多年等待的目光,再回望自己在佛门中的那段历程,他最终决定回归尘世,重新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
他的归来,在艺术圈引起了极大震动。那幅以1173万元成交的《转经图》,瞬间让所有对他怀疑的声音戛然而止,成为画坛的一个传奇。
和尚还俗,绝非易事。史国良的心路历程中藏着多少挣扎与无奈?他当初为何选择遁入空门?这十五年“画僧”生涯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?
---
尘世的牵挂终究难舍,画僧也终究还俗。
展开剩余92%2001年,远居加拿大的刘玉梅携儿子史村回国,专程前往河北柏林禅寺探望已做和尚十五年的史国良。面对阔别多年的妻儿,尽管身为出家人,史国良内心仍然涌起阵阵暖意。望着眼前那个离开时还是小不点,如今几乎和自己同高的儿子,他的内心泛起阵阵复杂的感慨。
1997年,他从美国归国后,便在河北柏林禅寺再度受戒。那段时间,寺院生活带给他无比的安宁与自在,仿佛超脱了世俗的纷扰,用更宽广、更慈悲的心境去体悟和观察世间万物。
寺中日常礼佛念经之后,他会时常外出采风,或静坐屋内潜心作画。出家前,史国良在绘画界已有一定名气,入佛门并未让他与世隔绝,反而通过参与佛教美术协会,拓宽了艺术交流的视野,也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。
他的画技和悟性让他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,成为多所高校美术系的客座教授,给学生们带来了不同凡响的艺术体验。
这十五年,史国良的生活可谓丰富而充实。然而,当他看到妻子日渐憔悴,听闻她的苦苦哀求,内心开始动摇。
刘玉梅含泪对他说:“儿子都长大了,也开始叛逆了。这些年你不在身边,我一个人根本管不了他了,你能不能回来,回来管管我们的儿子?”声音里满是哀伤和无奈。
史国良看着她这般模样,心中充满愧疚。曾经为了寻找灵感毅然“抛妻弃子”的自己,如今被深深的悔恨包围。望着对自己满眼陌生的儿子,血浓于水的父子关系竟如此疏离,令他心如刀割。
或许从那一刻起,史国良便暗自决定还俗。但他怕突如其来的变化会令妻子失望,于是含糊其辞地说:“我会好好考虑这件事。”
然而,还俗的计划因各种原因被搁置,整整十年过去,史国良却开始慢慢尝试与儿子重新建立联系。
对于史村而言,这位和尚父亲曾是遥远陌生的存在。他从小跟着母亲刘玉梅辗转中加两地,目睹母亲独自承受的辛劳。每当看到母亲望着史国良照片流泪,儿子对父亲的怨恨便愈加深重。
起初,他对父亲的示好充满抵触,甚至冷漠以对。史国良对此既难过又无奈,只能用耐心和时间一点点修复这段父子情。
幸好刘玉梅居中调解,尽管开头充满波折,但关系逐渐缓和,三人间的感情日渐亲密。
某次家庭聚会,看到儿子与父亲融洽相处,刘玉梅打破沉默:“国良,你还俗吧,我们一家人才能真正幸福,天天一起生活多好。”
面对家庭的温情,史国良沉默良久。自责和愧疚如潮水般涌来,他意识到自己享受着出家的安稳,所有家庭重担都由妻子独自承担。更有那隐藏多年的离婚事实,只有刘玉梅默默为双方家人遮掩,独自抚养史村。
眼含热泪,史国良终于点头答应还俗的请求。刘玉梅难掩激动与欣喜,久违的希望重新点亮她的生活。
那一刻,一家三口紧紧相拥,仿佛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考验,终于迎来了完整的团圆。
---
在一次访谈中,有记者问史国良:“出家意味着放下俗世的牵挂,您如何理解‘放下’二字?”
史国良回忆道星速优配,1995年初出家时有人问他:“你能放下吗?”他当时自信地说能。
那人又问:“你的妻子和孩子远渡加拿大陪伴你,你都能放下,那么你如何去爱众生呢?”这个问题令他无言以对。思索良久,他坦承其实自己放不下。
对方反问:“那你怎么能做和尚?”史国良说:“我这一生都处在一种模糊的中间状态,放不下亲情,也无法彻底出世。”
---
那么,一直放不下妻儿的史国良,为何会执意选择出家呢?
---
史国良生于1956年,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他家境贫寒,兄弟姐妹众多,吃饭都成问题。
他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,下面还有个年幼的弟弟。自认哥哥的他,总是偷偷把饭菜分给弟弟,导致自己营养不良,身材矮小,学校里也常被同龄人孤立。
他并不介意独处,反而喜欢一个人静静画画。用树枝、粉笔在地上描绘各种感兴趣的景象,毫无师承却能将画面表现得栩栩如生,显示出非凡天赋。
一次上课时,老师发现他在偷偷画课桌上的情景,惊叹他的绘画天赋,虽责备他不上课,却也破例放任。
时间流逝,史国良对绘画的热爱愈发浓烈。但他明白,家境困难,无力承担画画所需的花费。
父亲和哥哥姐姐们支持他追梦,这让他内心充满力量。
1973年,中学毕业的史国良被保送北京第三师范大学,师从著名画家周思聪,系统学习绘画技艺。天赋与勤奋并存,他很快在国画领域崭露头角。
毕业作品《新的一页》入选北京美术展,名师推荐他到黄胄、蒋兆和、李可染等名家门下深造。
在名师指导下,他的画技日益精进。1977年,20出头的他已创作多幅作品,并加入文化部国画创作组。
次年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研究生,潜心钻研,作品《月色》《山里人》广受赞誉。《月色》和《牧鸭》入选文化部国画展,《山里人》《藏区写生》参加习作展,成绩斐然。
1980年美院毕业展上,他的《八个壮劳力》《买猪图》获得高度评价,艺术事业蒸蒸日上。
---
毕业后,史国良任教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。浓厚艺术氛围中,他创作力旺盛。两年后,与刘大为、尚丁举办联合画展,四川美术学院为他举办个人国画展。
创作路虽顺,但艺术生涯难免遇瓶颈。
---
1985年,史国良调入北京中国画院,成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画家。院内高手如云,他深知自身不足,努力钻研。
同年,第23届蒙特卡洛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,他的《刻经》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,文化部亦颁发嘉奖,激励他持续创作,多次获奖。
1988年,他在台湾举办个人画展,名声远扬。
但随之而来的是创作上的迷茫与困顿,心态开始变化,难寻当年作画的畅快。
---
绘画的“瓶颈期”令他痛苦,无法释放心中情感。为寻新灵感,他决定出国走访,尽管妻子刘玉梅强烈反对。
两人于研读时相识相爱,结婚后,刘玉梅支持丈夫艺术事业,放弃职业成为全职主妇,辛苦抚养儿子。
丈夫远赴异国,她心中忐忑,却为丈夫坚持忍痛同意,未料这竟成出家导火索。
---
1989年到加拿大后,史国良经历语言障碍、孤独及种族歧视,生活艰难。一场交通事故让他伤痛难愈,肇事者逃逸,他无助报警却无果。
生病养伤期间,他多次电话求助妻子,刘玉梅带儿子赶来,生活稍有起色,却未见创作突破。
多年苦闷中,1995年,一位云游和尚的出现成转机。
他在温哥华偶遇星云大师,深受佛理启发,两人一见如故,长谈至深夜。
史国良萌生出家念头,认为脱离红尘,心灵方能净化,灵感亦将重现。他自幼对藏传佛教兴趣浓厚,星云大师成为他出家的重要机缘。
---
1995年,他不顾妻子哭求,随星云大师赴美国洛杉矶西华寺,进行为期一年的“三坛大戒”。
出家非易事,需经历严格戒律考验方获认可。虽肉体受苦,他的心灵却日益宁静。
刘玉梅目睹丈夫坚持,含泪签署离婚协议,决定暂时保密此事,独自撑起家庭。
---
寺庙生活并非理想,特别是在绘画方面,史国良偏好写实人像,反映现实生活,与寺庙注重佛像、山水等宗教题材南辕北辙。
这种理念冲突令他苦恼,终离开美国,回国内河北柏林禅寺再次受戒,开始长达十五年的修行生涯。
---
直到2010年,心中难舍亲情,史国良选择还俗,重回人间烟火。
---
多年修行沉淀星速优配,史国良的画技更臻成熟,作品中融合了虔诚信仰与人性情感,展现独特魅力
发布于:天津市配查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